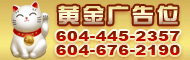他到底是极右还是极左?刺杀科克者的心理画像
那这本书究竟讲的是什么呢?霍弗在该书当中认为,极左和极右社会运动,看似彼此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构筑他们的成员、逻辑、运动方式和极端狂热性其实都是高度相似的。无论是一个失败的个体,还是一个失败的社会,都极有可能在一夕之间从推崇极左变为膜拜极右,或者刚好反过来。因为热衷于这些运动的人,他们其实并不执着于口号,他们酷爱其实仅仅是运动本身。
霍弗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二战前的德国,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当时是彼此针锋相对的,但有趣的是,两者的积极分子其实高度共享——一个因失业而愤怒的德国工人,可能昨天参加的还是德共的集会活动,义愤填膺的高喊打倒资本家。明天可能就以同样热情的投入到了纳粹党所煽动的仇犹运动中,被煽动着满大街砸犹太商店的玻璃、抓“苏联间谍”去了。
可能恰恰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共享性”,纳粹上台之后才于取缔其他党之前,先借国会山纵火案搞掉了德共,因为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曾提到,后者正在与他们争抢最广阔的动员库。所谓同行是冤家。
所以霍弗一针见血而又无比残酷的指出——狂热分子,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安安心心的当一个温和稳健的良善公民。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
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因为对他而言,他真正看重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主张、口号,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他借助激进运动、逃避自己卑微而失败的现实人生的那种诉求。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就像岳不群练得辟邪剑谱与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搭在一起一样,极左和极右社会运动其实一祖同宗。

真正南辕北辙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中的狂热分子与稳健派。要一个狂热的极左翼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难上加难。
《狂热分子》给这类群众运动的主体人群起了个名字,叫“畸零人”。所谓“畸零人”大约就是从社会中跌落的边缘人。他们因为在既有社会框架下无法认可自我,所以将矛头指向社会,投身于群众运动,试图使用集体的伟大来替换自己的失落感。
多说一句,读这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阿Q虽然看似跟“狂热分子”搭不上边,但那是因为鲁迅把他剖析的太深刻,让读者看透了他其实并不想献身于任何运动、而只是在卑微、自私的算计着自我。但实际你看阿Q的人生,生活失败、处于未庄社会的最边缘,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却迷茫无知。所以一会儿他看革命党杀头兴高采烈,另一会儿他却又突然高喊“革命了,革命了,我革命了”。
实际上阿Q既不忠于清廷,也不向往革命,他向往的只是激烈而非常规的社会运动能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颠覆性改变,或者至少这种期望给他的精神寄托。
所以他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也总是一夕之间。

 点个赞吧!您的鼓励让我们进步
点个赞吧!您的鼓励让我们进步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霍弗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二战前的德国,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当时是彼此针锋相对的,但有趣的是,两者的积极分子其实高度共享——一个因失业而愤怒的德国工人,可能昨天参加的还是德共的集会活动,义愤填膺的高喊打倒资本家。明天可能就以同样热情的投入到了纳粹党所煽动的仇犹运动中,被煽动着满大街砸犹太商店的玻璃、抓“苏联间谍”去了。
可能恰恰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共享性”,纳粹上台之后才于取缔其他党之前,先借国会山纵火案搞掉了德共,因为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曾提到,后者正在与他们争抢最广阔的动员库。所谓同行是冤家。
所以霍弗一针见血而又无比残酷的指出——狂热分子,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安安心心的当一个温和稳健的良善公民。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
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因为对他而言,他真正看重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主张、口号,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他借助激进运动、逃避自己卑微而失败的现实人生的那种诉求。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就像岳不群练得辟邪剑谱与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搭在一起一样,极左和极右社会运动其实一祖同宗。

真正南辕北辙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中的狂热分子与稳健派。要一个狂热的极左翼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难上加难。
《狂热分子》给这类群众运动的主体人群起了个名字,叫“畸零人”。所谓“畸零人”大约就是从社会中跌落的边缘人。他们因为在既有社会框架下无法认可自我,所以将矛头指向社会,投身于群众运动,试图使用集体的伟大来替换自己的失落感。
多说一句,读这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阿Q虽然看似跟“狂热分子”搭不上边,但那是因为鲁迅把他剖析的太深刻,让读者看透了他其实并不想献身于任何运动、而只是在卑微、自私的算计着自我。但实际你看阿Q的人生,生活失败、处于未庄社会的最边缘,想要改变自己的现状、却迷茫无知。所以一会儿他看革命党杀头兴高采烈,另一会儿他却又突然高喊“革命了,革命了,我革命了”。
实际上阿Q既不忠于清廷,也不向往革命,他向往的只是激烈而非常规的社会运动能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颠覆性改变,或者至少这种期望给他的精神寄托。
所以他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也总是一夕之间。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他到底是极右还是极左?刺杀科克者的心理画像
他到底是极右还是极左?刺杀科克者的心理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