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病了40年,才終於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
在這篇來自《環球科學》2025年5月新刊的文章中,我們將跟隨保羅·馬裡諾的講述,看看本文作者與不明症狀相伴數十年後,如何試圖找到自己與生俱來的異常行為出現的原因。
我預約了肯尼迪·克裡格研究所(Kennedy Krieger Institute)的神經科門診,它最初是一家專門治療腦癱兒童的機構,位於美國巴爾的摩市。我今年42歲,跨越了800多千米來到這座城市,是想要彌補童年時的缺憾——那時,我曾徒勞地探索一種科學界還知之甚少的神經現象。在赴約之前,我還有一些時間可以消遣。我順道去了醫院附近的喬治·皮博迪圖書館(George Peabody Library)。
圖書館有一個由大理石地板鋪就的巨大開放式中庭,四周聳立著六層華麗的新希臘式壁龕。我坐在一張木桌前,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一種強烈又熟悉的沖動突然湧起。我的身體像裝了馬達一樣開始“啟動”。就像平時一樣,我意識到自己正身處於公共場合,隨即抑制住了這種沖動。轉念一想,這本就是一次自我探索之旅,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大膽到可怕的念頭:如果我放任自己“啟動”會怎樣?我環顧四周:圖書管理員只身一人低頭給書籍蓋章,幾名游客仰頭凝視玻璃天花板。我在害怕什麼?
自我記事起,每當我感到興奮或全神貫注時,我就會做一件“事情”:抬起雙手,快速抖動手指,然後咧嘴皺眉做鬼臉,同時我的思緒開始遐想連篇——這就是我玩耍的方式。童年時的我在玩士兵小人模型時,不會像其他孩子一樣假裝它們是活生生的人,不會將正義的英雄砸向邪惡的反派。我只需簡單地把它們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然後“啟動”。我用“啟動”這個詞來描述我的肢體動作和驅動它們的精神能量。在我的腦海中,這些人物角色充滿能量:閃閃發光、生動逼真且富有電影感。這也是我畫畫的方式。每當我畫上一條線或添上一種顏色,我都會暫停動作開始“啟動”,在腦海中將所畫的對象想象成一個模型。
我的父母認為這只是小孩子的一種怪癖,等我長大了自然會停止這種行為。升入小學後,我似乎確實不再這麼做了。因為被人取笑,我開始下意識地壓抑這種沖動,但是這種沖動仍然會不斷在我心中湧起。只有當我遠離人們的視線,感覺安全時,例如關上了臥室或浴室的門,我才會讓這些積壓許久的沖動暴發。這種沖動從未減弱過,我幾乎每個時刻都抱有這種沖動,以至於我幾乎會忽視(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不過,“啟動”常常會分散我的注意力。高中時期,在做作業時,我常會因為歷史書中的場景而分心,經常需要一次次費力地從一行行文字中找回自己剛才讀到的地方。有一次我非常沮喪,就用透明膠帶把自己的手指綁了起來。
與此同時,挫折、焦慮或羞辱感也會讓我陷入一個由沉迷、情緒放大和生理興奮組成的反饋循環中。有很多個夜晚,我躺在床上希望自己快點入睡,但是這些湧起的沖動卻讓我汗流浹背、心跳加速,額頭由於雙手反復的摩擦而變得灼熱。

手指擺動是一種外在表現,是由馬裡諾腦海中發生的事情驅動的。他高度重復性的動作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沒有改變過。
最糟糕的是,因表裡不一而隨之產生的羞恥感。在別人面前,我表現得像個很酷的孩子——聰明、有趣、擅長運動、雖滿臉粉刺但相貌還算帥氣。但我也清楚一個殘酷的事實,我是個怪胎。一旦這個秘密暴露,我將羞愧難當,而與心愛的女孩在一起的那點微弱的希望,也將驟降為零。
我一次又一次地責備自己,發誓要戒掉它,但毫無效果。我以為自己一定是世界上唯一有這些舉動的人。
刻板行為的神經機制
我尋找答案的旅程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谷歌”這個詞都還沒出現。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小鎮上,我去看了一位兒科醫生。聽著我的講述,他點了點頭,又“嗯”了一聲,但手中的筆卻紋絲不動。我羞怯的描述聽起來似乎自相矛盾:“當我想象一些事物時,我的手就會出現這種行為。我不是故意這樣做的,我確實可以阻止它發生。”替他說句公道話,孩子們好動的天性和快速發展的大腦常讓人憂心忡忡,但這些在兒科醫生眼中早已司空見慣,並不會十分關注。事實上,即便他當時仔細調查,也不會有任何發現。
 點個贊吧!您的鼓勵讓我們進步
點個贊吧!您的鼓勵讓我們進步
 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我預約了肯尼迪·克裡格研究所(Kennedy Krieger Institute)的神經科門診,它最初是一家專門治療腦癱兒童的機構,位於美國巴爾的摩市。我今年42歲,跨越了800多千米來到這座城市,是想要彌補童年時的缺憾——那時,我曾徒勞地探索一種科學界還知之甚少的神經現象。在赴約之前,我還有一些時間可以消遣。我順道去了醫院附近的喬治·皮博迪圖書館(George Peabody Library)。
圖書館有一個由大理石地板鋪就的巨大開放式中庭,四周聳立著六層華麗的新希臘式壁龕。我坐在一張木桌前,在筆記本上塗塗寫寫,一種強烈又熟悉的沖動突然湧起。我的身體像裝了馬達一樣開始“啟動”。就像平時一樣,我意識到自己正身處於公共場合,隨即抑制住了這種沖動。轉念一想,這本就是一次自我探索之旅,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大膽到可怕的念頭:如果我放任自己“啟動”會怎樣?我環顧四周:圖書管理員只身一人低頭給書籍蓋章,幾名游客仰頭凝視玻璃天花板。我在害怕什麼?
自我記事起,每當我感到興奮或全神貫注時,我就會做一件“事情”:抬起雙手,快速抖動手指,然後咧嘴皺眉做鬼臉,同時我的思緒開始遐想連篇——這就是我玩耍的方式。童年時的我在玩士兵小人模型時,不會像其他孩子一樣假裝它們是活生生的人,不會將正義的英雄砸向邪惡的反派。我只需簡單地把它們放在面前的咖啡桌上,然後“啟動”。我用“啟動”這個詞來描述我的肢體動作和驅動它們的精神能量。在我的腦海中,這些人物角色充滿能量:閃閃發光、生動逼真且富有電影感。這也是我畫畫的方式。每當我畫上一條線或添上一種顏色,我都會暫停動作開始“啟動”,在腦海中將所畫的對象想象成一個模型。
我的父母認為這只是小孩子的一種怪癖,等我長大了自然會停止這種行為。升入小學後,我似乎確實不再這麼做了。因為被人取笑,我開始下意識地壓抑這種沖動,但是這種沖動仍然會不斷在我心中湧起。只有當我遠離人們的視線,感覺安全時,例如關上了臥室或浴室的門,我才會讓這些積壓許久的沖動暴發。這種沖動從未減弱過,我幾乎每個時刻都抱有這種沖動,以至於我幾乎會忽視(意識不到)它的存在。
不過,“啟動”常常會分散我的注意力。高中時期,在做作業時,我常會因為歷史書中的場景而分心,經常需要一次次費力地從一行行文字中找回自己剛才讀到的地方。有一次我非常沮喪,就用透明膠帶把自己的手指綁了起來。
與此同時,挫折、焦慮或羞辱感也會讓我陷入一個由沉迷、情緒放大和生理興奮組成的反饋循環中。有很多個夜晚,我躺在床上希望自己快點入睡,但是這些湧起的沖動卻讓我汗流浹背、心跳加速,額頭由於雙手反復的摩擦而變得灼熱。

手指擺動是一種外在表現,是由馬裡諾腦海中發生的事情驅動的。他高度重復性的動作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沒有改變過。
最糟糕的是,因表裡不一而隨之產生的羞恥感。在別人面前,我表現得像個很酷的孩子——聰明、有趣、擅長運動、雖滿臉粉刺但相貌還算帥氣。但我也清楚一個殘酷的事實,我是個怪胎。一旦這個秘密暴露,我將羞愧難當,而與心愛的女孩在一起的那點微弱的希望,也將驟降為零。
我一次又一次地責備自己,發誓要戒掉它,但毫無效果。我以為自己一定是世界上唯一有這些舉動的人。
刻板行為的神經機制
我尋找答案的旅程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谷歌”這個詞都還沒出現。在馬薩諸塞州的一個小鎮上,我去看了一位兒科醫生。聽著我的講述,他點了點頭,又“嗯”了一聲,但手中的筆卻紋絲不動。我羞怯的描述聽起來似乎自相矛盾:“當我想象一些事物時,我的手就會出現這種行為。我不是故意這樣做的,我確實可以阻止它發生。”替他說句公道話,孩子們好動的天性和快速發展的大腦常讓人憂心忡忡,但這些在兒科醫生眼中早已司空見慣,並不會十分關注。事實上,即便他當時仔細調查,也不會有任何發現。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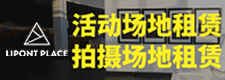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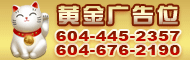



 他病了40年,才終於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
他病了40年,才終於知道自己經歷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