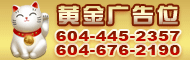[文章出轨] 许世瑛与陈寅恪:文章背后的学缘
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在1929年下半年被正式撤销,原任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改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随即在两系陆续开设了“佛经翻译文学”、“唐诗校释”、“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诗研究”、“欧阳修研究”、“《世说新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从罗香林、卞僧慧、王永兴、周一良、石泉等众多弟子日后的回忆中,不难了解他当时讲学课徒的具体情况。可惜迄今所见的记录绝大部分都出自历史系学生之手,很少有来自中文系学生的讲述,让人不免未惬于心。
历经劫难的陈寅恪病逝于1969年10月,消息辗转流传至海外,立刻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震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在次年3月出版的第十六卷第三期上集中刊登了数篇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敬悼陈寅恪老师》恰好出自毕业于清华中文系的许世瑛之手。倒是不妨借此转换视角,略窥义宁史学对中文系学生的沾溉。

陈寅恪许世瑛在1930年考入清华中文系,毕业后又继续在清华中文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直至1936年毕业离校。尽管就求学经历而言,他在校期间主要受知于刘文典、黄节、朱自清、俞平伯等中文系教授,与此同时又仰赖其父许寿裳的人脉关系,得到过鲁迅的悉心指点,“以后之成就,可以说得自鲁迅先生者甚大”(许世瑮《鲁迅与先父寿裳公的友情》,载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但在这篇悼念文章中却详尽地回忆了昔日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时的情景:“我很幸运,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听寅恪师讲课。……他讲课只是平铺直叙,但是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讲,既没有人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因为内容丰富而精采,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把它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如果再进一步参酌他的治学历程,更能够辨识出不少来源于陈寅恪的影响。
许世瑛在1945年撰写的《研究国学应走的途径》(载《读书青年》第二卷第一期)中现身说法:“大学文学院虽然有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的分别,可是这三系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是须臾不可离的。”虽然出身于中文系,但他当时撰写的不少论文并不局限于文学一隅,反而对史学问题很感兴趣,在关注焦点和考辨方式上都明显带有陈氏治史的风格。例如在《王羲之父子与天师道之关系》(载1944年《读书青年》第一卷第三期)
一文中,许世瑛开宗明义就直言:“从前陈寅恪师说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大多信奉天师道,而政治上的许多大变乱,像晋赵王伦之废立,宋范晔之谋反,及刘劭之弑逆,皆与天师道有密切关系(详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四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可说是不刊之论,值得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仔细玩味,换句话说,启发我们后辈的地方实在不少。”他提到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发表于1933年,同时还另有清华大学印行的单册本(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论着编年目录》,载蒋氏《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其用意当正如许世瑛在回忆中所述,“寅恪师每有一篇论文发表,他一定把单行本带来,分送给听课的同学”。陈氏在该文中专设一节考述“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其中说道:“琅邪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薰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盖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并以王羲之为中心,深入研讨了天师道信仰与书法创作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许世瑛正是从中得到启发,才会钩稽排比相关文献,着重考察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父子信奉天师道的具体表现。
有时候许世瑛并未明言,但通过比对覆按,仍能发现其立论的渊源所自。例如在稍后发表的《王导政绩和晋元帝中兴》(载1944年《读书青年》第一卷第六期)
中,他针对前人有欠公允的评论,重新考察了永嘉南渡之后王导的诸多政绩,认为“晋元帝能以帝室远支建都建业,上承西晋怀、愍末绪,下开东晋偏安江左之基,实在是王导辅翼之功”。在钩沉考索的过程中,他尤其强调王导在处理政务时能够顾全大局,为了结纳绥辑吴人而委曲求全:“王公尚有另一种长处,就是为了要达到固国本、绥土人的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即便自低身份,采用硁硁者流所不屑的方策。”清人王鸣盛曾诟病王导“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十七史商榷》卷五十“《王导传》多溢美”条),许世瑛能够不循旧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在陈寅恪编撰于三十年代的《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载《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9年)里,早就列有“东晋初中州人与吴人之关系”一讲,虽然没有展开具体论说,仅有“初至吴时,对吴人态度”、“封建乃镇抚吴人”、“王所畏之吴人”、“王导作吴语”等零星提示,但都是许氏考察的重点所在;而罗列的参考文献如《晋书》诸纪传和《世说新语》相关篇目等,也都在许氏征引讨论之列。陈寅恪在开设课程时自律极严,讲授的都是深造自得的内容,“一则以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与见解(包括古人的与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一则是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一则是以前已经讲过的也不愿再重复,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卞僧慧记录于1935年9月23日的《“晋至唐史”开课笔记》,载卞氏《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由此不难推断,许世瑛在构思撰作时,无论观点立意还是文献史料,都应该和陈寅恪的授课内容密不可分。
 不错的新闻,我要点赞
不错的新闻,我要点赞
 无评论不新闻,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无评论不新闻,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历经劫难的陈寅恪病逝于1969年10月,消息辗转流传至海外,立刻引起学术界极大的震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在次年3月出版的第十六卷第三期上集中刊登了数篇悼念文章,其中一篇《敬悼陈寅恪老师》恰好出自毕业于清华中文系的许世瑛之手。倒是不妨借此转换视角,略窥义宁史学对中文系学生的沾溉。

陈寅恪许世瑛在1930年考入清华中文系,毕业后又继续在清华中文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直至1936年毕业离校。尽管就求学经历而言,他在校期间主要受知于刘文典、黄节、朱自清、俞平伯等中文系教授,与此同时又仰赖其父许寿裳的人脉关系,得到过鲁迅的悉心指点,“以后之成就,可以说得自鲁迅先生者甚大”(许世瑮《鲁迅与先父寿裳公的友情》,载绍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但在这篇悼念文章中却详尽地回忆了昔日选修陈寅恪所开课程时的情景:“我很幸运,从大学三年级就开始听寅恪师讲课。……他讲课只是平铺直叙,但是听者并不感到枯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讲,既没有人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因为内容丰富而精采,大家都知道机会难得,不应该轻易把它放过。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如果再进一步参酌他的治学历程,更能够辨识出不少来源于陈寅恪的影响。
许世瑛在1945年撰写的《研究国学应走的途径》(载《读书青年》第二卷第一期)中现身说法:“大学文学院虽然有国文系、史学系、哲学系的分别,可是这三系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是须臾不可离的。”虽然出身于中文系,但他当时撰写的不少论文并不局限于文学一隅,反而对史学问题很感兴趣,在关注焦点和考辨方式上都明显带有陈氏治史的风格。例如在《王羲之父子与天师道之关系》(载1944年《读书青年》第一卷第三期)
一文中,许世瑛开宗明义就直言:“从前陈寅恪师说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大多信奉天师道,而政治上的许多大变乱,像晋赵王伦之废立,宋范晔之谋反,及刘劭之弑逆,皆与天师道有密切关系(详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四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可说是不刊之论,值得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仔细玩味,换句话说,启发我们后辈的地方实在不少。”他提到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发表于1933年,同时还另有清华大学印行的单册本(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论着编年目录》,载蒋氏《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其用意当正如许世瑛在回忆中所述,“寅恪师每有一篇论文发表,他一定把单行本带来,分送给听课的同学”。陈氏在该文中专设一节考述“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世家”,其中说道:“琅邪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薰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此盖以前读史之人所未曾注意者也。”并以王羲之为中心,深入研讨了天师道信仰与书法创作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许世瑛正是从中得到启发,才会钩稽排比相关文献,着重考察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父子信奉天师道的具体表现。
有时候许世瑛并未明言,但通过比对覆按,仍能发现其立论的渊源所自。例如在稍后发表的《王导政绩和晋元帝中兴》(载1944年《读书青年》第一卷第六期)
中,他针对前人有欠公允的评论,重新考察了永嘉南渡之后王导的诸多政绩,认为“晋元帝能以帝室远支建都建业,上承西晋怀、愍末绪,下开东晋偏安江左之基,实在是王导辅翼之功”。在钩沉考索的过程中,他尤其强调王导在处理政务时能够顾全大局,为了结纳绥辑吴人而委曲求全:“王公尚有另一种长处,就是为了要达到固国本、绥土人的目的,不惜用任何手段,即便自低身份,采用硁硁者流所不屑的方策。”清人王鸣盛曾诟病王导“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十七史商榷》卷五十“《王导传》多溢美”条),许世瑛能够不循旧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在陈寅恪编撰于三十年代的《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载《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9年)里,早就列有“东晋初中州人与吴人之关系”一讲,虽然没有展开具体论说,仅有“初至吴时,对吴人态度”、“封建乃镇抚吴人”、“王所畏之吴人”、“王导作吴语”等零星提示,但都是许氏考察的重点所在;而罗列的参考文献如《晋书》诸纪传和《世说新语》相关篇目等,也都在许氏征引讨论之列。陈寅恪在开设课程时自律极严,讲授的都是深造自得的内容,“一则以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与见解(包括古人的与今人的),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一则是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一则是以前已经讲过的也不愿再重复,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卞僧慧记录于1935年9月23日的《“晋至唐史”开课笔记》,载卞氏《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由此不难推断,许世瑛在构思撰作时,无论观点立意还是文献史料,都应该和陈寅恪的授课内容密不可分。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