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别人的繁华,走自己的路(图)
看别人的繁华,走自己的路

无论在职场上还是人生中,每个人都注定只能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方式或许更夺目、更成功、更妥帖,但自己的路才会让内心更舒适,未来更宽阔。
一
孙菲拣了一份工作。
之所以说拣,是因为她原本不在录用名单里——被录用的一位同学不来了,所以轮到了她。
这些,是孙菲在工作半年后才知道的。她所在的部门是公司刚成立的新媒体部,从主管到员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孙菲从小反应慢,小朋友们一起去游乐园,大家都是不管什么项目,先冲上去再说,她则默默地站在一边观察,直到确信自己会玩,才进去。母亲觉得她这样挺好的,至少谈恋爱不容易冲动。
等孙菲长大了,世界已经不是母亲眼里的那个世界,女孩子都在闯天下、干事业,“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彻底过时了。
孙菲自己也着急,像她这种慢热型,很容易被领导与同事误认为不够努力,更重要的是,她过于沉静,没有感染力。
吴美与孙菲相反。她只比孙菲早一周进公司,孙菲见到她的时候,还以为她至少在公司工作三五年了。如果说孙菲是太阳能热水器,需要一整天的光照缓慢升温,吴美就是即热型,自带小宇宙。
第一次讨论选题,吴美一口气说了10个,孙菲羡慕地望着她——有些选题,是孙菲想都不敢想的,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所以,她只报了一个,这是她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并且符合自家新媒体定位的。
散会后,主管老白暗暗佩服自己有眼光,吴美是他第一眼看中的,而孙菲只是候补顶位上来的,放在一个平台上,两人的能力高下立判。
因为只有一个选题,老白每天看着孙菲坐在那儿,就有点生气。吴美总是很忙,风风火火,她的热情燃烧了整个办公室,而孙菲就像是那一小块沙漠。
“孙菲,你干嘛呢?”老白问。“我在研究同行的文章。”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10次,老白懒得再问了。幸好,孙菲仅有的一个选题操作得不错,跌跌撞撞总算过了试用期。毫无悬念,吴美是试用期最闪耀的新员工,她点子多,做事麻利,有担当,虽然失误多一点,但老白深表理解,很少因此批评她。
二
公众平台上线一周年的时候,准备做一场线下活动。品牌提供的场地确定下来时,离活动开始只有3天时间了,大家都觉得印制请柬来不及了,即使是市区内寄送,也可能出现延误。
孙菲建议发送电子请柬,环保新颖,吴美说:“还是纸质的更有诚意,我负责搞定。”老白赞许地点点头,作为一周年庆这样隆重的活动,他当然希望嘉宾可以拿到一张精美的请柬作为纪念。
吴美能量全开,找到广告公司的朋友,连夜帮她印制了请柬,为防止快递延误,她让高中同学开着车,跑遍全市,终于在两天之内,把请柬全部送达了。
“干得漂亮!”老白说。
活动当天,嘉宾迟迟没有出现。离开场只差5分钟的时候,大家才弄明白,吴美把请柬上的地址印错了。现场一片慌乱,公车、私车全部动员出去,总算把嘉宾接到了会场,老白又累又气,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他忽然想起吴美在试用期的时候,文章标题里曾把“姝”写成“殊”,公号互推的时候,同一个二维码放过两遍,最过分的是有个广告,品牌名叫“狼毒”,她发出去的是“狠毒”……这么长时间了,她竟依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因为这件事,老白扣了吴美一个月奖金。
发工资的那天晚上,吴美喝醉酒,对同事小赵说:“我没有功劳有苦劳,老白太无情了。”
三
领导与下属关系很微妙。越是曾经彼此欣赏的人,当两人心生嫌隙时,达成谅解越难——因为曾经期望很高,如今失望更多。
请柬事件后,吴美变得保守了。有一天,她看着孙菲不紧不慢、从容地做着手里的活儿,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很傻,做得多错得多,她决定学习孙菲。
然而,老白却不习惯了,何况吴美的工作一直是以量取胜,粗疏的工作习惯让她在质上往往略逊一筹。而孙菲正相反,她在试用期满的第二个月,写出了一篇爆款文章,被600多个公号转发,老白习惯了她慢工出细活儿的工作节奏,平日要死不活,偶尔一鸣惊人。
吴美是负责调动老白兴奋神经的,孙菲则负责让老白安心。
对吴美的失望一天天累加,老白曾经对她送出过多少赞美,如今就有给出多少差评的欲望。更要命的是吴美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做得多错得多”是她永远的座右铭,做得又多又好,那是神仙。
谁都没想到,有一天,孙菲就成了这样的神仙。
那时候,吴美已经离职半年了。吴美的离职是冲动的结果,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老白告诉她,上个星期她负责的板块出了3次差错,在团队中差错率最高。吴美一冲动,忽然说:“我要辞职。”此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对老白存了这么大的怨气。一开始被当作宠儿的人,受不了有一天变成了普通人。
吴美离职后,孙菲接替了她的工作。老白原本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想到孙菲看上去毫不费力地就把两个人的活儿都做了,并且做得又快又好,失误率几乎为零。
老白好奇,就问孙菲:“做了这么久,觉得微信公众平台最重要的是什么?”孙菲回答:“不要跟读者玩花样,老老实实,垂直、精准地推送内容。”老白在心里默默地点了赞。
如果说职场是登山,吴美是一开始就被空运到了山顶,忽然前后左右都变成了下坡路。而孙菲是站在山脚下的人,她用了3个月考查地形,又用了3个月锻炼身体,然后开始登山;每一步都踩得踏踏实实,登山的路探得清清楚楚;她知道登山的困难,所以珍惜自己的每一点进步,享受每一阶段的风景。
四
公司决定开发周边产品的时候,老白毫不犹豫起用孙菲做了项目负责人。他想象成熟了的孙菲会像过去的吴美,雷厉风行,很快交出让他满意的答卷。然而他每天路过孙菲的工位,孙菲都在不紧不慢地摆弄堆在桌子上的各种笔记本、钥匙扣,她甚至经常不在办公室,说是考察市场,谁知道是干嘛去了。
看着慢悠悠的孙菲,有一天,老白忽然有些想念吴美,这个风风火火的下属不知如今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重复高开低走的老路?
在职场里,短跑用的是冲动与体力,长跑用的是智慧与耐力。
一个项目初创的时候,需要“短跑运动员”营造氛围,不管事情做得怎么样,至少他们有热情,够热闹,让人产生红红火火的错觉,而当项目走上正轨,就是“长跑运动员”的天下了。
想到这儿,老白觉得职场真残酷。
老白耐着性子,每天给自己喝心灵柴鸡汤,像呼唤原力觉醒一样等待孙菲充电。孙菲那边却死一般寂静,老白问:“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孙菲总是回答:“还在准备。”
老白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等下去,他甚至想再招聘一个像吴美那样的短跑选手,每天在自己面前蹦蹦跳跳,指哪儿打哪儿,让他不至于没有安全感。
就在这时,孙菲却忽然冲进来递给他一本手账。“交作业。”她说。老白翻开手账,看完,忍不住在心里赞叹:“真漂亮!”
这就是孙菲,做她的领导,要耐得住寂寞。
上司,都喜欢事无巨细向他汇报、每一天都有新点子、新发现的员工,然而最终走得最远的,往往是起初默默无闻的那个——没有太多时间说话,才有更多时间思考,把热情、能量蓄积起来,一点一点释放。
——摘自故事帝网
二
沙漠的尽头是大海
沈泽清
很多年后,有人问起:“你会弹琴?”我回答:“是的,我会弹琴。”我既没有成名成家,甚至没有赖以为生。弹琴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像会写字、会游泳一样。
但一开始,妈妈并不是这么想的。
一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那里永远是是相同的模样,所有人之间似乎都认识。
于是,“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比你家贝贝小的孩子,都开始学琴了”……大概就是这样的理由,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的。更何况,弹钢琴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
那年,《茜茜公主》的电影刚刚热播,之后留给妈妈一个深藏内心的公主梦,可在那个家里孩子还要为了吃饱饭而打架的年代,这些怎么可能实现呢?
那年我四岁半,被“夹带”进学前班,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妈妈29岁,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交车去银川看琴,直线距离近100公里。那时候柏油路还没修好,单程都要4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又走过无数遍。
“我当年真喜欢那个12000元的苏联进口钢琴啊,你爸就在旁边劝,说借的钱太多,家里太困难了。”
“我觉得我的琴已经很不错了。德国原厂的产线,晚几年的琴还远不如我的呢。”长大后我这样安慰妈妈。
“嗯……也行吧。”
二
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爸爸和他七八个朋友热热闹闹地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具抬上3楼。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包裹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5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嗯!”
后来我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7点到9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
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全程监督。
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水一次,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弹错音会被打手。
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每天最少两小时,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10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完成业余10级的考试。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他们,当初曾是我妈妈买琴的动力。“这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嘛!”他们会这样自我安慰,只有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最高级。
“妈妈,为什么慧子她们都不学了,我还要学?”
“这是你答应我的。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
三
从上世纪90年代“学琴潮”开始,如郎朗父亲一样的家长绝不是特例,带着孩子背井离乡,就为了儿子能在中央音乐学院找“最好的音乐老师”,考音乐附小、附中,从此走向“钢琴家”之路。当然,郎朗是个特例。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作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从来对此坚信不疑,“海顿教出了莫扎特,莫扎特教出了贝多芬。”
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4个小时。
银川的钢琴课每周一次,周日早晨7点整,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
中午将近12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4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天已黑透。路上的近8个小时只为一个小时的“专业课”。
下课之后,母女俩同吃一份“露露快餐厅”的5元快餐,踏上返程路。
冬天好冷,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
夏天好闷,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交车上,我满身都起了痱子。
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我总是什么都想要——一切都那么好看、那么新鲜,但到头来也什么都不可能买。
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学费一次50元,(还有)吃饭、来回车费,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内。”
很多年过去,在某个饭局上,有人说:“你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简直是疯了。”
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可是转过身去,我莫名地想要流眼泪。
四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挨打变得很频繁,后来我还问过爸爸:“你以前为什么从来不进卧室看我弹琴?你不喜欢吗?”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对我说:“太惨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伴随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似乎这件“高贵”的兴趣爱好无法让我家任何一个人从中获得“轻松”与“喜乐”。
常常伴随着的,是抽泣声和严厉的训斥声,每首曲子想过关都需要巨大的付出。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掌,似乎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
爸爸偶尔进来劝两声,但多半都是沉默的,在妈妈的执着下,他“救”不了我,我知道。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被反锁在家里,要完成当天的“任务”。有的时候只是锁一个晚上,寒暑假的时候会是一整个早晨或者下午。虽然寂寞,却是我难得的休闲时间。
在闭锁的空间里,我弹5分钟琴,转悠5分钟,翻翻童话书,和自己说说话。电视是不敢看的,因为看过的电视机会发热。
有那么一两个暑假,也有同学来找我,我没有钥匙出不去,她也进不来,两个小姑娘就坐在地上,隔着房门聊天,我不时看看表,提醒她:“你得回去了,我妈要回来了。”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发呆,看着外面偶尔飞过的鸟、寥寥无几的行人从家门口经过。沙尘暴吹过的时候,闭上眼睛,我总感觉自己听到了海的浪涛声,“沙漠的尽头就是大海呢!”
五
“疯女人带着娃娃去银川学琴”的故事延续了5年,我家终于搬到了银川。考过6级,妈妈再也认不清愈发复杂的五线谱,我也不再需要她从头盯着我弹到尾。8级的曲子很好听,9级好难,10级我不太有把握……
这些问题随着初中青春期的叛逆变得非常模糊。
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终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
“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自己过去近10年的重心完全放错了位置。”妈妈无比惋惜,“女孩子将来搞个艺术,多好!又轻松又温柔!”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正常孩子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
这是我的“硬伤”。
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那样的话,既不像妈妈学理科那么辛苦,又不像爸爸学文科那么平淡——我终于没有获得妈妈期望我获得的。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
六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琴伴奏,我想去呢!”
“妈妈,学校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
“妈妈,钢琴比赛我被刷掉了……有个师姐弹了肖邦那首特别难的练习曲,好好听啊!”
“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人们在教堂结婚,我弹婚礼进行曲!”
“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我好久没去了。”
“妈妈,我想弹琴。”
……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过去10年的琴凳生涯对接上了。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让我在往后学习文学、艺术、历史时,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
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
这种对接,或者说和解发生得自然而然,我完全没法想象,抛弃了这段童年——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童年——我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如此向妈妈“告白”的时候,她只是说:“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好傻。”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我租的房子里一直没有钢琴。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只学会了一两首新曲子,是趁每年回家的那几天,断断续续学的。旧钢琴一直摆在新家的书房里,上面铺着雪白的蕾丝花布,琴身依旧闪着黑色的耀眼的光芒。
我最后一次给外婆弹琴是大一的暑假,我弹了德彪西的《月光》,外婆说:“真好听,好温柔啊!”那时候她正饱受癌症的煎熬。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采访”了妈妈,视频里面母女俩还没讲多久,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我们不管怎样都没法解释和安抚的情绪。
我快29岁了,正是妈妈送我学琴的年纪。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那样,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日复一日地为一个人云亦云的“孩子需要有一个特长”或者说是为自己难以企及的梦想辛苦奔波。
在视频里我数次想对她说:虽然我没有走向她为我铺设的美好人生,但这么多年过去后,我明白,自己最终收获的,远比曾经付出的多。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
——摘自“大不六”文章网
三
生命的顶峰不是用来攻克的
侯文咏
一
我第一次见识到大众传播的威力是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那时,作为一个麻醉科医生,我却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声名鹊起。
有一次,我被安排参加一个知名的访谈节目,因为那时侯我写的《亲爱的老婆》正畅销。两个礼拜后,节目在全台湾的电视网播了出来。
我记得节目刚一播完,母亲就打来电话说:“你上电视了,你知不知道?”她显得很兴奋,“很多亲戚都看到了,打电话来恭喜你爸爸和我。”
隔天开始,情况更加激烈了,一连好几天,不管我跟对方熟不熟悉,只要他们一见到我,都很乐于向我提起:“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了你……”
渐渐,邀请我以作家的身份去参加演讲、接受采访或者上广播、上电视的机会越来越多。
我开始从书本上那几行作者简介中跳出来,变成了活生生可以被辨认得出来的作家。
最先出现的怪事是:路上的陌生人开始跟你打招呼了。他们不但打招呼有时还能够谈论你生命中的某些细节。在我有限的人生里,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不曾发生的。
我原来工作的医学界,有保守、低调的传统。除非你得到了某种专业上的肯定,到了主任、教授这样的位置,否则,你就没有对外发言的资格。任何违背这个传统在媒体上出风头的人都意味着浮夸、随便。
有一次,医院高层找我谈话。领导说:“我们最近和人事行政局开会,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人手、更好的待遇……”
“当然应该。”我说。
“但人事行政局的长官很不以为然,会议中有个人说:‘你们医院有个医生侯文咏,他可出名了!既然他有那么多时间写文章,还上电视、广播节目,我看你们的医师不太辛苦,也不太累吧……’”
“可是,我利用的是自己休假的时间。”
“节目不一定在休假的时间播出,大家也未必都是休假的时候看到……一般人并不了解这些细节。”
虽然领导试图绕圈子,可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都怪我爱出风头,害了大家。
我想,他其实一定想直截了当地这样骂:“你难道不能像别人一样,乖乖地做你该做的事,好好地保持医生的本分且受人尊敬吗?”
我记得我参加麻醉专科医生的审核考试,最后一关的面试中,有一位委员半开玩笑地问我:“你写作这么畅销,版税收入这么丰富,大概不太需要这张专科证书吧?”
说真的,这个带着轻蔑意味的问题差点让我从椅子上跌下来。
二
我就这样搭着顺风车,书本一路畅销。一会儿被选入年度成
功人物,什么青年才俊,又是什么年度畅销作家、最受欢迎的风云人物。也有商业杂志分析我是如何成功地使用媒体及公关策略……
还有一次,我接受了一个报纸的采访,隔天我看到那篇报道兴致勃勃地“塑造”了一个不世出的年轻天才作家。这个作家几岁就开始写文章,又是如何天才般地以高分轻易考上医学院,如何轻松地一面行医、一面写作……
除了报道旁边配着的我的照片及我的名字外,我简直无法辨认专访里描述的那个人就是我了。
我的照片被刊在许多杂志的显要之处,书店的大型广告牌上……不知为什么,我看着,一种罪恶感油然而生,我很怕忽然有人看不下去了,跳出来指着说:“内容物与标识不符。”
当时的感觉是,我的处境有点像躺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不管从医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衡量,我感觉自己要不是太高,就是太矮,始终难以适应这张床,哪个方面我都需要扭曲自己一点点,好配合这张床。
这种情况有点尴尬,一方面我并不觉得舒服,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家都恭喜我成功了啊!成功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三
那时候我在想,这种无所适从或许是因为我还不够成功,配不上现在的名气。于是我激励自己,做更多,做更好。
我花更多时间,咬紧牙关多写作、多演讲、多看病人、多做研究、多写医学论文、还考进了研究所。
有一阵子,我桌上的座右铭就写着:“Do better to be equal.(你必须做得更好才有机会平等)”
这样,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主治医生,进入研究所攻读博士,一路高升,被指派参与政要医疗小组。
同时,越来越多的新书进入畅销排行榜,被邀请主持、参与各式各样的电视、广播节目。
我越发努力,结果我有了更多邀约、门诊,更多的医学论文发表、实验室的工作、手术室的工作,以及医学院的学生和课程……
我忙得团团转。那时候,我的研究助理必须为我准备便当。我总是站着吃便当,拿着便当走来走去,接电话、指示一些未完成的事情。
往往饭吃到一半,被别的事情打断,又放下了便当。打断我的事可能是手术室的病人,也可能是实验室用的老鼠来源有问题……
等我处理完,我又忘了原来的便当顺手丢到哪里了。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我根本忘记了我到底吃没吃过饭。
我吃饭没滋味,活着也没有太多心情。生活好像永远有追不完的行程,一个接着一个。印象中我总是在迟到、取消行程、打电话道歉。我知道有人能接受我的道歉,有人不肯原谅,但是我无可奈何,不愿、不能、也无力改善。
我去签售,面对拥挤的、满怀热情的读者和如雷的掌声,我在想,我过去所相信的或者是被说服的值得奋斗的人生,似乎都是为了迈向这一刻而假设的。
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充满掌声的场合时,却发现这样的生命如此空洞。
我突然醒悟,不管我变成了主治医生、博士、作家、教授……再多的头衔,如果它们并不指向更深刻而愉悦的生命,那么这一切,只不过是顺应某种虚浮的价值所累积出来的废墟罢了。
四
春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和朋友一起去攀爬玉山。我们在冷冽的空气中欣赏沿途的风光。
登到峰顶时,我本以为会有一种征服了玉山的成就感或快感,可我却被一种更宽阔的感动深深震撼。
那样的感动来自山峦起伏、流水、树木、路边的野花、气味,甚至是鸟叫的声音。
那时候,我理解了我并不是为了攻顶而来。不管我攻克了多高的山峰,我生命中所能拥有的不过是那段美好的经验。山一直在那里,所有的景物也一样,它们不被谁所征服,我也征服不了什么。
那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点点美丽的心情。
我想,或许我必须先停下来,暂时跳脱此时此地的自己、自己熟悉的环境或者观点,直到时间足够长,距离足够远,我才能有宽广的视野看到更多本质的东西,或者是自己深藏的内在。
于是我打开历史,背起行囊,试着跟不熟悉的人、事、文明与情感对话。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展开了属于自己内在与外在的旅程。
36岁那年,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向医院主管递上了我的辞呈。我的主管非常讶异,问我:“你做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想走了?是不是对医院有什么不满意?”
我笑了笑,摇摇头。
“离开这里,你打算去哪里?”我的主管问。
“我想写作。”
“写作?”他似乎有些不理解,“写作收入比医生高出很多吗?”
我又摇摇头,“写作收入不稳定。”
“那你为什么要走?”
“我只觉得……我不年轻了,今后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来源《我的天才梦》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鼓励
 无评论不新闻,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无评论不新闻,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吧

无论在职场上还是人生中,每个人都注定只能走自己的路。别人的方式或许更夺目、更成功、更妥帖,但自己的路才会让内心更舒适,未来更宽阔。
一
孙菲拣了一份工作。
之所以说拣,是因为她原本不在录用名单里——被录用的一位同学不来了,所以轮到了她。
这些,是孙菲在工作半年后才知道的。她所在的部门是公司刚成立的新媒体部,从主管到员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孙菲从小反应慢,小朋友们一起去游乐园,大家都是不管什么项目,先冲上去再说,她则默默地站在一边观察,直到确信自己会玩,才进去。母亲觉得她这样挺好的,至少谈恋爱不容易冲动。
等孙菲长大了,世界已经不是母亲眼里的那个世界,女孩子都在闯天下、干事业,“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彻底过时了。
孙菲自己也着急,像她这种慢热型,很容易被领导与同事误认为不够努力,更重要的是,她过于沉静,没有感染力。
吴美与孙菲相反。她只比孙菲早一周进公司,孙菲见到她的时候,还以为她至少在公司工作三五年了。如果说孙菲是太阳能热水器,需要一整天的光照缓慢升温,吴美就是即热型,自带小宇宙。
第一次讨论选题,吴美一口气说了10个,孙菲羡慕地望着她——有些选题,是孙菲想都不敢想的,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到。所以,她只报了一个,这是她觉得自己有把握做好,并且符合自家新媒体定位的。
散会后,主管老白暗暗佩服自己有眼光,吴美是他第一眼看中的,而孙菲只是候补顶位上来的,放在一个平台上,两人的能力高下立判。
因为只有一个选题,老白每天看着孙菲坐在那儿,就有点生气。吴美总是很忙,风风火火,她的热情燃烧了整个办公室,而孙菲就像是那一小块沙漠。
“孙菲,你干嘛呢?”老白问。“我在研究同行的文章。”
这样的对话重复了10次,老白懒得再问了。幸好,孙菲仅有的一个选题操作得不错,跌跌撞撞总算过了试用期。毫无悬念,吴美是试用期最闪耀的新员工,她点子多,做事麻利,有担当,虽然失误多一点,但老白深表理解,很少因此批评她。
二
公众平台上线一周年的时候,准备做一场线下活动。品牌提供的场地确定下来时,离活动开始只有3天时间了,大家都觉得印制请柬来不及了,即使是市区内寄送,也可能出现延误。
孙菲建议发送电子请柬,环保新颖,吴美说:“还是纸质的更有诚意,我负责搞定。”老白赞许地点点头,作为一周年庆这样隆重的活动,他当然希望嘉宾可以拿到一张精美的请柬作为纪念。
吴美能量全开,找到广告公司的朋友,连夜帮她印制了请柬,为防止快递延误,她让高中同学开着车,跑遍全市,终于在两天之内,把请柬全部送达了。
“干得漂亮!”老白说。
活动当天,嘉宾迟迟没有出现。离开场只差5分钟的时候,大家才弄明白,吴美把请柬上的地址印错了。现场一片慌乱,公车、私车全部动员出去,总算把嘉宾接到了会场,老白又累又气,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他忽然想起吴美在试用期的时候,文章标题里曾把“姝”写成“殊”,公号互推的时候,同一个二维码放过两遍,最过分的是有个广告,品牌名叫“狼毒”,她发出去的是“狠毒”……这么长时间了,她竟依然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因为这件事,老白扣了吴美一个月奖金。
发工资的那天晚上,吴美喝醉酒,对同事小赵说:“我没有功劳有苦劳,老白太无情了。”
三
领导与下属关系很微妙。越是曾经彼此欣赏的人,当两人心生嫌隙时,达成谅解越难——因为曾经期望很高,如今失望更多。
请柬事件后,吴美变得保守了。有一天,她看着孙菲不紧不慢、从容地做着手里的活儿,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很傻,做得多错得多,她决定学习孙菲。
然而,老白却不习惯了,何况吴美的工作一直是以量取胜,粗疏的工作习惯让她在质上往往略逊一筹。而孙菲正相反,她在试用期满的第二个月,写出了一篇爆款文章,被600多个公号转发,老白习惯了她慢工出细活儿的工作节奏,平日要死不活,偶尔一鸣惊人。
吴美是负责调动老白兴奋神经的,孙菲则负责让老白安心。
对吴美的失望一天天累加,老白曾经对她送出过多少赞美,如今就有给出多少差评的欲望。更要命的是吴美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做得多错得多”是她永远的座右铭,做得又多又好,那是神仙。
谁都没想到,有一天,孙菲就成了这样的神仙。
那时候,吴美已经离职半年了。吴美的离职是冲动的结果,有一天下班的时候,老白告诉她,上个星期她负责的板块出了3次差错,在团队中差错率最高。吴美一冲动,忽然说:“我要辞职。”此时,她才发现原来自己对老白存了这么大的怨气。一开始被当作宠儿的人,受不了有一天变成了普通人。
吴美离职后,孙菲接替了她的工作。老白原本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想到孙菲看上去毫不费力地就把两个人的活儿都做了,并且做得又快又好,失误率几乎为零。
老白好奇,就问孙菲:“做了这么久,觉得微信公众平台最重要的是什么?”孙菲回答:“不要跟读者玩花样,老老实实,垂直、精准地推送内容。”老白在心里默默地点了赞。
如果说职场是登山,吴美是一开始就被空运到了山顶,忽然前后左右都变成了下坡路。而孙菲是站在山脚下的人,她用了3个月考查地形,又用了3个月锻炼身体,然后开始登山;每一步都踩得踏踏实实,登山的路探得清清楚楚;她知道登山的困难,所以珍惜自己的每一点进步,享受每一阶段的风景。
四
公司决定开发周边产品的时候,老白毫不犹豫起用孙菲做了项目负责人。他想象成熟了的孙菲会像过去的吴美,雷厉风行,很快交出让他满意的答卷。然而他每天路过孙菲的工位,孙菲都在不紧不慢地摆弄堆在桌子上的各种笔记本、钥匙扣,她甚至经常不在办公室,说是考察市场,谁知道是干嘛去了。
看着慢悠悠的孙菲,有一天,老白忽然有些想念吴美,这个风风火火的下属不知如今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重复高开低走的老路?
在职场里,短跑用的是冲动与体力,长跑用的是智慧与耐力。
一个项目初创的时候,需要“短跑运动员”营造氛围,不管事情做得怎么样,至少他们有热情,够热闹,让人产生红红火火的错觉,而当项目走上正轨,就是“长跑运动员”的天下了。
想到这儿,老白觉得职场真残酷。
老白耐着性子,每天给自己喝心灵柴鸡汤,像呼唤原力觉醒一样等待孙菲充电。孙菲那边却死一般寂静,老白问:“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孙菲总是回答:“还在准备。”
老白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等下去,他甚至想再招聘一个像吴美那样的短跑选手,每天在自己面前蹦蹦跳跳,指哪儿打哪儿,让他不至于没有安全感。
就在这时,孙菲却忽然冲进来递给他一本手账。“交作业。”她说。老白翻开手账,看完,忍不住在心里赞叹:“真漂亮!”
这就是孙菲,做她的领导,要耐得住寂寞。
上司,都喜欢事无巨细向他汇报、每一天都有新点子、新发现的员工,然而最终走得最远的,往往是起初默默无闻的那个——没有太多时间说话,才有更多时间思考,把热情、能量蓄积起来,一点一点释放。
——摘自故事帝网
二
沙漠的尽头是大海
沈泽清
很多年后,有人问起:“你会弹琴?”我回答:“是的,我会弹琴。”我既没有成名成家,甚至没有赖以为生。弹琴只是一个普通的技能,像会写字、会游泳一样。
但一开始,妈妈并不是这么想的。
一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油田小镇,那里永远是是相同的模样,所有人之间似乎都认识。
于是,“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比你家贝贝小的孩子,都开始学琴了”……大概就是这样的理由,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的。更何况,弹钢琴是多么“高贵”的一件事!
那年,《茜茜公主》的电影刚刚热播,之后留给妈妈一个深藏内心的公主梦,可在那个家里孩子还要为了吃饱饭而打架的年代,这些怎么可能实现呢?
那年我四岁半,被“夹带”进学前班,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妈妈29岁,和爸爸月工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交车去银川看琴,直线距离近100公里。那时候柏油路还没修好,单程都要4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又走过无数遍。
“我当年真喜欢那个12000元的苏联进口钢琴啊,你爸就在旁边劝,说借的钱太多,家里太困难了。”
“我觉得我的琴已经很不错了。德国原厂的产线,晚几年的琴还远不如我的呢。”长大后我这样安慰妈妈。
“嗯……也行吧。”
二
钢琴搬回家的场景我还记得。爸爸和他七八个朋友热热闹闹地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的大家具抬上3楼。小小的家里围了很多人,包裹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妈妈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贝贝,这是你5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学,听见没?”“嗯!”
后来我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搬进家门的,是一些铁律:所有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7点到9点固定练琴两个小时。
妈妈会坐在我的旁边,从开始的音阶,到每一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和节拍,全程监督。
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水一次,并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弹错音会被打手。
从钢琴进门到我初中毕业,每天最少两小时,几乎全年无休,重大考试、比赛前练琴时间会尽可能延长。
10年周而复始,一直到我完成业余10级的考试。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他们,当初曾是我妈妈买琴的动力。“这不过是一个兴趣爱好嘛!”他们会这样自我安慰,只有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最高级。
“妈妈,为什么慧子她们都不学了,我还要学?”
“这是你答应我的。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
三
从上世纪90年代“学琴潮”开始,如郎朗父亲一样的家长绝不是特例,带着孩子背井离乡,就为了儿子能在中央音乐学院找“最好的音乐老师”,考音乐附小、附中,从此走向“钢琴家”之路。当然,郎朗是个特例。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作为高中老师的妈妈,从来对此坚信不疑,“海顿教出了莫扎特,莫扎特教出了贝多芬。”
可小镇上会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的三两个音乐老师。只有去市里——百公里的土路,单程近4个小时。
银川的钢琴课每周一次,周日早晨7点整,妈妈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就一路抱着我。
中午将近12点到银川南门老汽车站,坐3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半个多小时到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4点原路返回,晚上到家天已黑透。路上的近8个小时只为一个小时的“专业课”。
下课之后,母女俩同吃一份“露露快餐厅”的5元快餐,踏上返程路。
冬天好冷,常常开始上课了,我的手仍像冻坏的胡萝卜。连钢琴老师都有些不忍,倒杯热水让这对大风里来的母女俩先暖一暖。
夏天好闷,母女俩昏昏沉沉地挤在公交车上,我满身都起了痱子。
每当拉着妈妈的手走在银川宽阔的马路上,我总是什么都想要——一切都那么好看、那么新鲜,但到头来也什么都不可能买。
妈妈的理由不容置疑:“学费一次50元,(还有)吃饭、来回车费,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100元以内。”
很多年过去,在某个饭局上,有人说:“你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简直是疯了。”
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可是转过身去,我莫名地想要流眼泪。
四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挨打变得很频繁,后来我还问过爸爸:“你以前为什么从来不进卧室看我弹琴?你不喜欢吗?”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对我说:“太惨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伴随琴声的欢笑声寥寥无几,似乎这件“高贵”的兴趣爱好无法让我家任何一个人从中获得“轻松”与“喜乐”。
常常伴随着的,是抽泣声和严厉的训斥声,每首曲子想过关都需要巨大的付出。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掌,似乎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
爸爸偶尔进来劝两声,但多半都是沉默的,在妈妈的执着下,他“救”不了我,我知道。
在往后的很多年中,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怎么会有小朋友喜欢这件枯燥、乏味又痛苦的事情呢?那时候的我着实难以理解。
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会被反锁在家里,要完成当天的“任务”。有的时候只是锁一个晚上,寒暑假的时候会是一整个早晨或者下午。虽然寂寞,却是我难得的休闲时间。
在闭锁的空间里,我弹5分钟琴,转悠5分钟,翻翻童话书,和自己说说话。电视是不敢看的,因为看过的电视机会发热。
有那么一两个暑假,也有同学来找我,我没有钥匙出不去,她也进不来,两个小姑娘就坐在地上,隔着房门聊天,我不时看看表,提醒她:“你得回去了,我妈要回来了。”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趴在阳台的窗户上发呆,看着外面偶尔飞过的鸟、寥寥无几的行人从家门口经过。沙尘暴吹过的时候,闭上眼睛,我总感觉自己听到了海的浪涛声,“沙漠的尽头就是大海呢!”
五
“疯女人带着娃娃去银川学琴”的故事延续了5年,我家终于搬到了银川。考过6级,妈妈再也认不清愈发复杂的五线谱,我也不再需要她从头盯着我弹到尾。8级的曲子很好听,9级好难,10级我不太有把握……
这些问题随着初中青春期的叛逆变得非常模糊。
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在妈妈数次征询意见之后,终于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
“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自己过去近10年的重心完全放错了位置。”妈妈无比惋惜,“女孩子将来搞个艺术,多好!又轻松又温柔!”
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正常孩子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
这是我的“硬伤”。
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上音乐学院附中、考上北京或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表演系,那样的话,既不像妈妈学理科那么辛苦,又不像爸爸学文科那么平淡——我终于没有获得妈妈期望我获得的。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
六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竟然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琴伴奏,我想去呢!”
“妈妈,学校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
“妈妈,钢琴比赛我被刷掉了……有个师姐弹了肖邦那首特别难的练习曲,好好听啊!”
“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人们在教堂结婚,我弹婚礼进行曲!”
“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远,我好久没去了。”
“妈妈,我想弹琴。”
……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过去10年的琴凳生涯对接上了。
我无比感激童年的每一首钢琴曲的学习——从维也纳古典乐派到浪漫主义,让我在往后学习文学、艺术、历史时,不断彼此影响和融通;
感激童年无数枯燥乏味的练习,让所有的技巧成为我的肢体与记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感激那些独自在家的日子,让我早早地不那么惧怕孤独和别离,并在往后的生活中一直充满浪漫与幻想。
这种对接,或者说和解发生得自然而然,我完全没法想象,抛弃了这段童年——或者说几乎是整个童年——我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如此向妈妈“告白”的时候,她只是说:“小时候管你弹琴管得太严了,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好傻。”
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我租的房子里一直没有钢琴。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只学会了一两首新曲子,是趁每年回家的那几天,断断续续学的。旧钢琴一直摆在新家的书房里,上面铺着雪白的蕾丝花布,琴身依旧闪着黑色的耀眼的光芒。
我最后一次给外婆弹琴是大一的暑假,我弹了德彪西的《月光》,外婆说:“真好听,好温柔啊!”那时候她正饱受癌症的煎熬。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采访”了妈妈,视频里面母女俩还没讲多久,眼泪就流了下来,这是我们不管怎样都没法解释和安抚的情绪。
我快29岁了,正是妈妈送我学琴的年纪。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想自己未必能有勇气和毅力像妈妈那样,付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10年,日复一日地为一个人云亦云的“孩子需要有一个特长”或者说是为自己难以企及的梦想辛苦奔波。
在视频里我数次想对她说:虽然我没有走向她为我铺设的美好人生,但这么多年过去后,我明白,自己最终收获的,远比曾经付出的多。感谢妈妈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话刚到嘴边,我就哽咽了。
——摘自“大不六”文章网
三
生命的顶峰不是用来攻克的
侯文咏
一
我第一次见识到大众传播的威力是第一次上电视的时候。那时,作为一个麻醉科医生,我却以畅销书作家的身份声名鹊起。
有一次,我被安排参加一个知名的访谈节目,因为那时侯我写的《亲爱的老婆》正畅销。两个礼拜后,节目在全台湾的电视网播了出来。
我记得节目刚一播完,母亲就打来电话说:“你上电视了,你知不知道?”她显得很兴奋,“很多亲戚都看到了,打电话来恭喜你爸爸和我。”
隔天开始,情况更加激烈了,一连好几天,不管我跟对方熟不熟悉,只要他们一见到我,都很乐于向我提起:“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了你……”
渐渐,邀请我以作家的身份去参加演讲、接受采访或者上广播、上电视的机会越来越多。
我开始从书本上那几行作者简介中跳出来,变成了活生生可以被辨认得出来的作家。
最先出现的怪事是:路上的陌生人开始跟你打招呼了。他们不但打招呼有时还能够谈论你生命中的某些细节。在我有限的人生里,这种现象以前是从来不曾发生的。
我原来工作的医学界,有保守、低调的传统。除非你得到了某种专业上的肯定,到了主任、教授这样的位置,否则,你就没有对外发言的资格。任何违背这个传统在媒体上出风头的人都意味着浮夸、随便。
有一次,医院高层找我谈话。领导说:“我们最近和人事行政局开会,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人手、更好的待遇……”
“当然应该。”我说。
“但人事行政局的长官很不以为然,会议中有个人说:‘你们医院有个医生侯文咏,他可出名了!既然他有那么多时间写文章,还上电视、广播节目,我看你们的医师不太辛苦,也不太累吧……’”
“可是,我利用的是自己休假的时间。”
“节目不一定在休假的时间播出,大家也未必都是休假的时候看到……一般人并不了解这些细节。”
虽然领导试图绕圈子,可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都怪我爱出风头,害了大家。
我想,他其实一定想直截了当地这样骂:“你难道不能像别人一样,乖乖地做你该做的事,好好地保持医生的本分且受人尊敬吗?”
我记得我参加麻醉专科医生的审核考试,最后一关的面试中,有一位委员半开玩笑地问我:“你写作这么畅销,版税收入这么丰富,大概不太需要这张专科证书吧?”
说真的,这个带着轻蔑意味的问题差点让我从椅子上跌下来。
二
我就这样搭着顺风车,书本一路畅销。一会儿被选入年度成
功人物,什么青年才俊,又是什么年度畅销作家、最受欢迎的风云人物。也有商业杂志分析我是如何成功地使用媒体及公关策略……
还有一次,我接受了一个报纸的采访,隔天我看到那篇报道兴致勃勃地“塑造”了一个不世出的年轻天才作家。这个作家几岁就开始写文章,又是如何天才般地以高分轻易考上医学院,如何轻松地一面行医、一面写作……
除了报道旁边配着的我的照片及我的名字外,我简直无法辨认专访里描述的那个人就是我了。
我的照片被刊在许多杂志的显要之处,书店的大型广告牌上……不知为什么,我看着,一种罪恶感油然而生,我很怕忽然有人看不下去了,跳出来指着说:“内容物与标识不符。”
当时的感觉是,我的处境有点像躺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不管从医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衡量,我感觉自己要不是太高,就是太矮,始终难以适应这张床,哪个方面我都需要扭曲自己一点点,好配合这张床。
这种情况有点尴尬,一方面我并不觉得舒服,可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家都恭喜我成功了啊!成功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三
那时候我在想,这种无所适从或许是因为我还不够成功,配不上现在的名气。于是我激励自己,做更多,做更好。
我花更多时间,咬紧牙关多写作、多演讲、多看病人、多做研究、多写医学论文、还考进了研究所。
有一阵子,我桌上的座右铭就写着:“Do better to be equal.(你必须做得更好才有机会平等)”
这样,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主治医生,进入研究所攻读博士,一路高升,被指派参与政要医疗小组。
同时,越来越多的新书进入畅销排行榜,被邀请主持、参与各式各样的电视、广播节目。
我越发努力,结果我有了更多邀约、门诊,更多的医学论文发表、实验室的工作、手术室的工作,以及医学院的学生和课程……
我忙得团团转。那时候,我的研究助理必须为我准备便当。我总是站着吃便当,拿着便当走来走去,接电话、指示一些未完成的事情。
往往饭吃到一半,被别的事情打断,又放下了便当。打断我的事可能是手术室的病人,也可能是实验室用的老鼠来源有问题……
等我处理完,我又忘了原来的便当顺手丢到哪里了。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我根本忘记了我到底吃没吃过饭。
我吃饭没滋味,活着也没有太多心情。生活好像永远有追不完的行程,一个接着一个。印象中我总是在迟到、取消行程、打电话道歉。我知道有人能接受我的道歉,有人不肯原谅,但是我无可奈何,不愿、不能、也无力改善。
我去签售,面对拥挤的、满怀热情的读者和如雷的掌声,我在想,我过去所相信的或者是被说服的值得奋斗的人生,似乎都是为了迈向这一刻而假设的。
我没有想到,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充满掌声的场合时,却发现这样的生命如此空洞。
我突然醒悟,不管我变成了主治医生、博士、作家、教授……再多的头衔,如果它们并不指向更深刻而愉悦的生命,那么这一切,只不过是顺应某种虚浮的价值所累积出来的废墟罢了。
四
春天的时候,我有机会和朋友一起去攀爬玉山。我们在冷冽的空气中欣赏沿途的风光。
登到峰顶时,我本以为会有一种征服了玉山的成就感或快感,可我却被一种更宽阔的感动深深震撼。
那样的感动来自山峦起伏、流水、树木、路边的野花、气味,甚至是鸟叫的声音。
那时候,我理解了我并不是为了攻顶而来。不管我攻克了多高的山峰,我生命中所能拥有的不过是那段美好的经验。山一直在那里,所有的景物也一样,它们不被谁所征服,我也征服不了什么。
那时候,我开始有了一点点美丽的心情。
我想,或许我必须先停下来,暂时跳脱此时此地的自己、自己熟悉的环境或者观点,直到时间足够长,距离足够远,我才能有宽广的视野看到更多本质的东西,或者是自己深藏的内在。
于是我打开历史,背起行囊,试着跟不熟悉的人、事、文明与情感对话。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展开了属于自己内在与外在的旅程。
36岁那年,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向医院主管递上了我的辞呈。我的主管非常讶异,问我:“你做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想走了?是不是对医院有什么不满意?”
我笑了笑,摇摇头。
“离开这里,你打算去哪里?”我的主管问。
“我想写作。”
“写作?”他似乎有些不理解,“写作收入比医生高出很多吗?”
我又摇摇头,“写作收入不稳定。”
“那你为什么要走?”
“我只觉得……我不年轻了,今后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来源《我的天才梦》
| 分享: |
| 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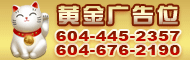




 看别人的繁华,走自己的路(图)
看别人的繁华,走自己的路(图)